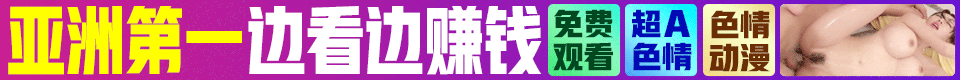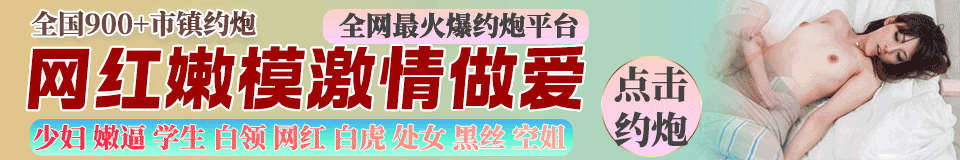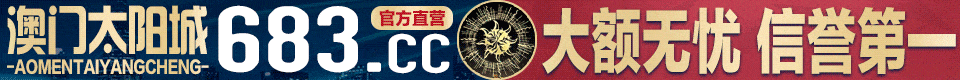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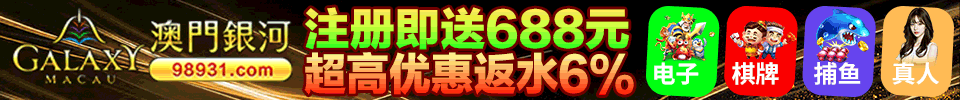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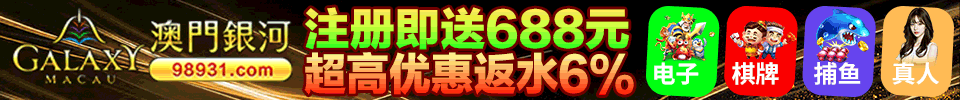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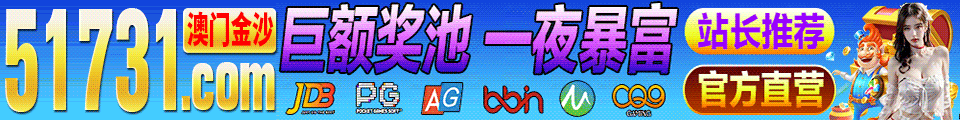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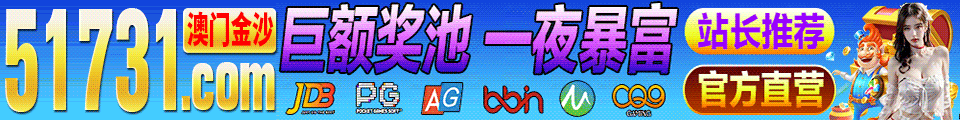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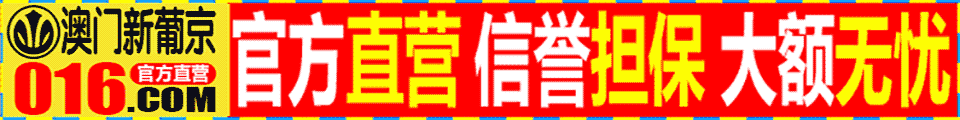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东北大炕】(精修版)(01)作者:998
作者:998
字数:17395
yZWnxHpb.png.
点击看大图
改编方向:肉戏增强细节以增加代入感,剧情设定全面大修,方向是纯爱向。
所以原著大姐被肥猪男黑又硬爆奸的桥段做了大幅度修改,但仍旧有郁闷情节。
不过我之所以保留郁闷情节,是为了主角爆种「宰杀」肥猪男做准备,而且
大姐身心都不会背叛主角,详细见正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致敬原作者!
第一节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非常偏僻落后的山村,我家爹娘、两个姐姐再加上我一共
是五口人。
早年间,男女婚嫁早,特别是穷乡僻壤的东北山沟里。娘在16岁的时候便嫁
给了爹,第二年就生下了我大姐,在我娘19岁的时候又生了我二姐,原本计划生
育的问题,爹娘他们应该不能再生了。
不过农村非常封建,女娃不算传宗接代是常识,这个观念在这个年代牢牢盘
踞在所有人脑海里。爹是村里最大的官——村支书,虽然同样也有着这个观念,
但顾及自己的身份,也就不敢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不过,在二姐出生两年后,亲戚朋友村人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当
这些言语传到爷爷奶奶姥娘姥爷耳中时,四老立刻冒着风雪从百里之外翻山越岭
的赶到我家,据那时只有四五岁的大姐回忆,当时爷爷奶奶指着娘亲骂,而姥爷
姥娘则指着爹来骂,骂了一阵后,他们又调转来开导自己的子女。
虽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但是事后一年,我就哇哇叫着来到这个世界。虽
然事后听说当时的爹和娘都被人抓走动了什么手术,而且爹的公职也被革去了。
但是当为我的百日进行摆酒的时候,爹和娘以及四个老人都腰杆挺直,满脸红光,
喜气洋洋的接待着乡亲们。
在我出生后,据说再也没有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了,那段时间爹娘也算扬眉吐
气,在村人面前神色都很傲然。不过因为爹的公职没了,除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外,再也没有什么收入,生活开始艰难起来,爹和娘那骄傲的神色也不见了。
为了养活五张嘴,爹一咬牙,离开了这个乡村,外出务工了。家里就留下娘
和我们三姐弟。
不过,虽然家里只剩下娘一个妇道人家和三个幼童。但是由于爹在外面打工
很顺利,每半年回来一次的时候总是带了许多礼物和蛮丰厚的生活费回来。我们
家又在村人当中威风了起来,而我家也是全村第一户把泥房换成水泥房的。再加
上爹爹以前当村支书时留下的威望,在村里是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们这些妇幼的。
过了一两年,当爹爹带回全村第一台彩电的时候,全村都轰动了,调试彩电
的时候,几乎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了,把屋里屋外都挤得满满的。
过完年,爹爹又出去打工,不过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出去,而是全村青壮男丁
都跟着走了。这样一来整个村子只剩下些老弱妇幼了,而我母亲精明能干,为人
处世又面面俱到,与乡亲们相处的非常好,大家都很佩服她,所以连带的,我娘
的声望在村里也达到了最高点。
甚至很多时候,我娘的话比村支书还有用。
而我就是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在这个可以说是女儿村的村子里长大的。
我们东北自古以来就有个习惯,这个习惯现在虽然没有什么人、特别是城里
的人去做,但是在我们这个常年风雪封地,地处偏僻的封闭乡村却依然保持着。
这个习惯就是脱光衣服睡觉。
据老人说,这样脱光了钻进棉被,躺在热炕上,那感觉比穿着衣服暖多了,
同时也舒服多了。当然,不用说都是一人一张被子。
小时候的事,我记得不大清楚,只是朦胧记得,我打小就没有自己的被子,
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被娘抱在怀里,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娘的被子是家里最大的,
据大姐说,娘的被子是和爹一起用的,所以才这么大。
在爹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跟娘亲一起睡,转而跟大姐睡一张被子。每当爹在
家的时候,而且在我晚上憋尿憋醒的时候,就会看到娘的大被子动个不停,而且
还传来爹和娘急促的喘息声。我喊尿尿的时候,原本非常疼爱我的爹都会骂我,
因为娘总会起来帮我尿尿。
我不知道两个姐姐有没有看过这一幕,反正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发现姐
姐们都一动不动的睡着觉,也许她们看到了,却因为怕被爹爹骂而不敢出声打扰
爹娘吧。于是当我自己能够小便的时候,我就没有打扰过他们,只是偷偷的钻下
床自己解决了。
我家的炕是个大炕,能够并排睡上3 个大人,挤一点线 个人也能睡下。床
上只摆了娘和两个姐姐的三张被子,所以说还蛮宽敞的。当时我最想要的就是能
够拥有自己的被子,但是娘老是说我还小又爱踢被,怕我着凉,就不同意我自己
睡。
那时我真的很讨厌跟娘亲睡,因为她总不让我乱动,还总是喜欢摸着我小鸡
鸡睡。不过当我10岁时发生了一件事后,我就不再提起要被子的事。
这要细讲。
当时村子里没有小学,村中的小孩要上学都要走上十多里路,才能到乡里的
小学上学。但是我们这里一年中有6 个月是下雪的日子,所以村里很多小孩,特
别是女孩都是推迟读书或者干脆不读。
不过,不知道爹常年在外见多识广还是家里有点闲钱,我们姐弟三人都早早
就上学了,我十岁就读小学四年级了。而大我三岁的二姐则读六年级,大我五岁
的大姐在镇里的中学读初三。在这年,娘才32岁。
说起我娘,我打小就特别粘她,因为娘亲不光温柔贤惠,还是十里八乡出了
名的大美人。而男性不分年龄……不,应该说不管男女,不论年龄,所有人都必
不可免的以貌取人,我也不例外,所以我那么黏娘也可能是因为娘太美了。
娘具体美到什么程度呢?
一米七多的高挑身段,乌瀑般的秀发搭配标准的瓜子脸盘,一双远山般的柳
叶弯眉下是善睬明眸,不点而赤的绛唇温润如玉,而生育过三个儿女的身材却因
为常年劳作不显丝毫走形,反而是火辣曼妙。
而且托三次生育的福,妈妈的乳量也跟着三次哺乳期水涨船高,盆骨也愈发
扩张,再加上本就不是骨感型的女人,屁股肉很多,导致臀部丰腴到夸张的地步。
我总觉得娘的屁股就像父亲过年时带回来的大寿桃,又圆又大。
当然,也不像普通短腿农妇那样臃肿,因为妈妈身条高,一双腿还特别长,
所以相同的大屁股放到妈妈身上自然看起来要协调的多,不让人感觉如普通中年
村妇那样倒胃口,反而给人极致火辣的视觉冲击,引人欲火膨胀。
如此完美的娘亲,在农村长期风吹日晒的环境中,更是逆天到连肤色都是雪
白雪白的,仿若凝脂。不过这种在日光下晃眼的肤色虽然稀少,但也属于常见,
特别是东北。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见过,眼馋过这种白雪肌肤的美人。
相应的,美到冒泡的娘亲怎么可能不招蜂引蝶,丈夫又长年不在家,肯定是
那些男人打歪主意、意淫的首要目标。
但娘亲在当地属于书香门第的闺秀,姥爷起的名都让人感觉很文雅——姚溪。
姥爷是个骨子里骄傲的文化人,在那个年代可了不得,娘跟着耳濡目染,久而久
之自也沾染了这种文人的傲骨。
娘面对村里的大老粗,一直有种微不可查的优越感,平时除了必要的事很少
跟他们打交道,这就杜绝了娘变心的可能。
更不用提我还有个当过兵的爹爹,爹没大本事怎么能娶了娘呢?虽然他个头
连娘亲高都没有,但脾气暴躁可是闻名乡里,年轻时候在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勇
斗狠,早早就拼了一身凶名。
即便现在爹不如从前强势,但余威犹存,所以谁敢打我娘的主意都要好好掂
量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现实生活波澜不惊,淡如水。爹外出务工的这么些年也没什么狗血的事情发
生,毕竟穷乡僻壤的地方没什么巨屌的能人存在,我母亲的态度也是密不透风,
让人无缝可钻。所以有些男人即便看的再心痒,再意动,顶多也就是过过嘴瘾,
说两句骚话。
往事随风而去,如今村里都是些老头和毛孩子,青壮都走了,剩下三瓜俩枣
的老流氓小色鬼之流,也就盯着母亲的背影过过眼瘾,连正视都难。
至于偶有从乡镇慕芳名而来的色中恶鬼,他们也只是过来套套近乎,饱饱眼
福,看没什么空子钻也都灰溜溜的走了。也不敢上演什么恶霸强行欺辱的桥段,
因为住过农村的都懂,特别是非常落后的山沟沟,村民面对外来的人都是很团结
的,特别是我妈跟村里人相处的也好,再有我爹这个能人多年积威在村里留下的
号召力,到时候真有不开眼的找茬,收拾起来还不一呼百应?
虽然爹还没娘亲高,但我们三姐弟的身材却也非常标准,而且样貌也同样的
出色,没办法,我爹模样不差,母亲更是高挑娇美,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当然也遗
传了这些优秀基因。
话又说回来,也可能是东北人普遍都不矮,我十岁就有一米四五了,而十三
岁的二姐居然差不多一米六,十五的大姐更是厉害,比母亲也矮不了多少,那高
挑的身姿略显单薄,却更突出纯真清新的少女气质。
不知道是不是爹爹往年带回来的营养品太补,还是怎么的,两个姐姐的身躯
虽然单薄,也都有了女性曲线,虽然离成熟尚早,与妈妈比更是火柴梗的存在,
但还是非常能够吸引少男们的目光。
我们姐弟三人的感情非常好,也许打小在我接受爹爹特别给我的礼物后,我
都会把这些礼物分给姐姐的原因。不知道怎的,我从来没有独占的欲望,所有单
独给我的东西我都和姐姐们分享,像那些特别买来给我吃的营养品,我也毫不吝
啬的和两个姐姐一起享用。
我更是从来没有跟她俩吵过架,也从来没有红过脸。我对家人性子柔,心也
细,如此就越发讨两个姐姐欢心了。还有因为从小经常裸着睡在一起的原因,似
乎没了衣服的阻碍,敞开心扉对我们三姐弟而言更容易,姐姐们特别喜欢跟我说
心里话,长此以往感情如胶似漆。
我也很有男人的担当。有一次我打架了,我把学校里对我说脏话的人打得灰
头土脸。和我同学校的二姐,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时候没少教训我。虽然二姐和
老师都问我打人的原因,但是我没有回答,我想那个被我打的学生也不会说出为
什么会被我打。
老师见问不出来,只好让我抄10遍课文当作处罚。我当然无所谓了,不过二
姐明显知道我不会随便打人的,所以一走出办公室,二姐就把我拉到偏僻的角落。
二姐用双手捧着我的脸,清汤挂面的素丽脸蛋满是心疼,然后紧紧地盯着我的眼
睛,没有说什么就是这样静静看着。
姐姐的眼睛很灵动,忽闪忽闪的像会说话,我跟姐姐的亲密程度自然知道她
想问我为什么打架,但是我不想那些污言烂语传入二姐的耳中,所以我把眼神望
向远处,决定不吭声。
没有得到答复,二姐突然笑了,笑得很美,让我莫名心动,但对两性一无所
知的我不知道那是渴望拥有她的悸动。姐笑意盈盈的盯着我瞅了半响,末了带点
小埋怨的轻声:「是不是你那同学用脏话骂你,你才教训他的?」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现在骂人的话一般都是肏你妈,尻你老母,干你妈
臭嗨等等,不过可能是我的姐姐太美丽又经常见到,所以那些和我争执的人在骂
我的时候很常说什么「肏你姐的屄,插死你姐姐」等等。
虽然这些话我不大懂,相信说这些话的小孩也不懂,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
种很严重的侮辱行为,毕竟大人生气时候都这么骂。
知道不是善意,还涉及家人,我的反应就会很过激,谁敢那么骂我,我便抄
起拳头就上去干架,也不管打不打得过。久而久之,我凭着这股狠劲让周遭的人
都不敢骂我了。当然,这样一来我也没有什么朋友了。至于那个被我狠扁一顿的
家伙,是刚转学来的。
姐姐当然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二姐也不多问,心里却很受用,于是温柔的拍
了拍我的脸蛋,有些爱不释手的摩挲着,软乎乎的说道:「人家刚转学就被你打
了个下马威,估计以后再也不敢在你面前说脏话了。」说完,突然又虎着脸敲了
下我的脑袋,也不舍得用力,转而嗔怪:「不过下次不准再打架了,多疼呀,骂
你你可以告诉老师嘛,你这样打来打去伤了谁都不好,是不是?」
也不知道二姐天性如此还是天生早熟的缘故,她不像大姐那般活泼调皮,心
智很早熟,又非常懂事,所以平时很能说动我,我很听她的话。
但我在原则问题上却很犟,我想都没想就摇了摇头,也没想过骗姐姐。
二姐也不多说,只是撅撅嘴,气呼呼的翘着食指指尖在我额头上戳了几下,
算是惩罚,「我就不告诉娘了……回头哪里疼我给你揉揉。」
轻描淡写的,这事就算完了。
我们这地势恶劣,很多学生的家离学校又很远,所以这里中午都不回家,大
家都带了午餐的食盒来学校吃。我刚和二姐一起吃着便当的时候,学校的高音喇
叭突然传来校长的声音,让学生立刻回教室集中。
回到教室听了广播,才知道连续不断的暴风雪又要来了,学校开始提前放学,
同时在暴风雪没有过去的时候,不用来学校,一律在家自习。在这个严冬季节,
我们这一带这样的事很常见,有时候期末考试都会因此取消。
暴风雪对于学生们来说,又要过几天无聊的日子了。因为风雪一来的时候,
连门都出不去,别说找同伴玩耍了。教室里一片唉声叹气。
我兴致也不高,有气无力的被二姐牵着离开学校后,立刻往家里赶。在这片
风雪之地生活的人,就是三岁小孩也知道暴风雪的恐怖,没有哪个白痴会在回家
路上玩耍。
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读初中的大姐也回来了,而娘亲看到家里人都回来了,不
由松了口气,开始忙着去烧炕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无论吃饭、聊天、睡觉都是
在炕上的。平时被子都折叠好放在依墙而建的橱柜里,只有晚上睡觉才移走矮桌
拿出来摊好。
我脱下厚重的毛衣棉靴,爬上了炕,先打开了炕头放着的电视,然后才把作
业拿出来放在矮桌上,当然跟上来的二姐一下子把电视关掉,没好气的瞪了我一
眼,也拿出了作业。
我明白二姐是要我先完成作业才准看电视,于是我只吐了吐舌头就写起作业
来。而大姐则和娘亲开始准备度过几天暴风雪的工作,去整理粮食,检查门窗等
等。
当我完成作业后,发现二姐早就完成了,她没有开电视看,只是一手托着香
腮,一手无意的绕着鬓角的青丝,看着一本故事书。我就是喜欢二姐这么体贴人,
忙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向二姐高喊作业写完了,因为我知道二姐其实是很喜欢看电
视的。
夜幕慢慢的降临了,外面的风声也越来越大,不过我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寒冷,
嘴里是热乎乎的晚饭,屁股下是暖烘烘的热炕,眼睛看到的是电视里的精彩节目。
这样的我怎么会去在乎外面冷不冷呢?一家四口吃完饭后,都坐在热炕上一
边看着电视,一边闲聊着。我依在大姐怀里,突然觉得这就是幸福啊。可是我对
幸福的感悟突然变成了深刻理解什么是不幸,因为突然停电了。
郁闷啊,这对我而言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小孩子都怕黑,我也不例外。整个房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同样也一阵
死寂般的宁静。年幼的我马上感觉到了恐怖。
我连忙向大姐的怀里拱,恐惧的环住姐姐柔若无骨的腰肢,立刻紧紧地抱住,
但是突然被大姐拧了一下脸颊,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我的脸贴在大姐柔软的胸脯上,
虽然大姐穿着厚棉袄,但是我仍能感觉到大姐的胸部鼓鼓的,好像在里面藏了两
个馒头。
我不知道黑暗中大姐脸红了,大姐也没推开我,一边调皮的捏住我鼻翼不让
我呼吸,一面问道:「娘,蜡烛在哪?」娘说道:「在墙角最下的抽屉里,你的
作业没有做吗?」大姐说:「在学校就做完了,二妹你们的作业呢?」说着指间
夹住我鼻翼,撸我鼻尖。
「哎呀疼……娘,姐欺负人!」真的疼,火辣辣的,大姐真的特别能作。
「刘宓,别欺负你弟弟。」娘习惯性的全名称呼。可能因为都长大了,娘除
了爱喊我乳名,对两个姐姐都是直接喊大名。
大姐撒娇似的哼了一下,放过了我的鼻子,却也没把我推开。
「作业都做了吧?」娘又问。
我和二姐回答,「做完了。」
娘一听便道:「那就不用找蜡烛了,睡觉吧,反正也没什么事。」我听到这
话不干了,忙喊道:「娘,现在才8 点多,那么早睡干嘛?可能是保险丝烧了,
等下会有电来的。」我才不想这么早睡,晚上9 点钟的时候3 频道会播动画片呢。
大姐看我着急就开心,脆生生的笑出声,好像引颈啼鸣的黄鹂,继而又捏住
我鼻子的戏谑:「哟,你怎么知道保险丝烧了?就算烧了,外面风大雪大的,你
叫谁去换呀。」
二姐也跟着搭腔:「小孩子晚上8 点就要睡觉了,这是书上说的。」说着二
姐跟妈妈已经摸黑打开橱柜,取出被子开始摊起来,大姐是闲不住的人,又来呵
我痒痒。
家人都习惯,也就任我俩闹作一团。
窸窸窣窣的铺盖声,片刻娘温柔的道:「来睡觉吧。」
我那里乐意,黑暗中瘪瘪嘴,却也不过去,无声的抗议着。
娘可疼我了,十分耐心的哄着:「我们的保险丝几天前才刚换的,而且你看
外面看不到一点灯光,一定是大雪把电线压断了,不说今天晚上没电来了,暴风
雪在的这几天都可能不来电,你呀,趁早过来睡吧,要是睡不着的话,娘跟你说
说话。」
我听到这话,心都凉了,以前就有过一次大雪压断了电线,那次一直过了好
几个星期,才有人把电线接好。没办法,谁叫我们这里交通很不便利,还异常偏
僻。不说现在暴风雪肆虐,就是暴风雪过后,那些供电局的也要等膝盖深的大雪
融化后才会来。
我心情跌落谷底,沉默不语。家里人都很了解我,知道我肯定是在生闷气,
于是你一言我一句的哄我,直到二姐答应下完雪出去跟我堆雪人,我才离开大姐,
悄悄蹭到墙角脱起了衣服。
虽然现在一片漆黑,姐姐和娘也在整理被子,而且我懂事以来,家里人都是
熄了灯以后才脱衣服进被子的,但是我就是害怕被人看见。
也许有人问,你一个小孩有什么好怕的?家里人一定在你小时候仔细看过你
的身体,你还有什么不敢给她们看的?
其实一个月前我都还敢光明正大的脱衣服,但是现在我不敢了,因为我小鸡
鸡上面肚子的地方,居然长了毛!我的同学去尿尿的时候,我都偷偷留意过,他
们根本没有长毛,而且我的小鸡鸡居然比他们大了两倍有余。
还有最近上体育课爬竿的时候,小鸡鸡受到挤压,虽然隔着厚厚的棉裤,但
仍能感受到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那感觉让人有点不自在,又有点期待。
这种感觉我连最亲密的二姐都没有说,我不是一个喜欢向长辈求救的人,但
是我知道一定是爹爹带回来的几盒小瓶饮料有关,我只记得那名字是什么激素,
当时爹怕我随他长不高,硬逼着我喝了。该不会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吧?
当然,让我最烦恼的还是小鸡鸡附近的毛。刚开始我那光滑的地方只是长了
一两根毛,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只是偷偷用剪刀剪掉了。但是过没几天,哪里居
然长出了数十根!吓得我小心的全部剪掉,但是跟着而来的是生毛的地方特别痒,
痒得我时不时要去瘙一下。既要瘙痒,又怕被人看见了笑话,那感觉还真是难受。
不过在那些毛又一次长出来的时候,那种痒痒的感觉消失了。我也知道,只
要剪掉那些毛我就会痒,而且那些毛长出来也不会妨碍我尿尿,所以我就没有再
去剪掉它了。脸皮薄的我不希望家人知道我那长毛,所以才会这样躲在角落脱衣
服。
此时娘喊道:「狗儿,脱了衣服没有?脱了就快进被子,免得着凉了。」狗
儿是我的小名,是我众多小名中最不喜欢的,但娘特别爱这么喊。其实我蛮喜欢
娘喊我小三这个小名,但是娘就说喊贱一点,我才会平安无事的长大。
我光着身子也觉得有点冷了,要不是在热炕上,我早就感冒了。所以我连忙
摸黑的往娘那边爬去,我不敢用走的,一怕踩到人,二怕绊倒。由于娘是睡在最
外边的,而我则习惯面对橱壁脱衣服,所以要爬着经过姐姐的地盘。姐姐们好像
非常熟悉我这个打小就养成的习惯动作,都不约而同,好像例行公事似的,拍了
拍我的屁股。
大姐偶尔还会揪我鸡鸡玩,但最近都被我躲开了,这次也不例外。
经过了这么久,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但是外面是晚上,而且还没有月
光,只能朦朦胧胧看到一个影子。看到最大的那个影子掀开被子向我招手,已经
开始有点冷的我,忙加快动作,先滚进了被窝。
「哇,好舒服,好暖哦。」我光溜溜的身体接触到被炕暖的被子,马上舒服
的喊道。
大家都只是笑了一下没有搭话,听窸窸窣窣的声音,不用想,就知道娘和姐
姐开始脱起衣服来了。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一股冷风进来,看来是娘掀开被子准
备进来了。
我不由侧转身朝姐姐那边挪动了一下,我从长毛后一直这样,因为怕娘不小
心碰到我那些毛,这样不就被她知道了?这可是我感觉丢人的秘密啊。
娘进来躺下后,发现由于我挪开了身子,搞得被子中间出现了入风的空隙,
于是像最近一样跟着挪动丰腴的娇躯,贴了上来,并微微撑起身子,伸出一只玉
臂从我身上掠过,紧了紧我这边的被子。
把被子整理的密实后,娘的那只手顺势把我抱住,然后娘的整个身躯都贴了
上来。娘的这个动作,让她那高耸丰满的肥乳,在我赤裸的背部磨擦了数次,可
以清晰感觉到两颗软中带硬、弹性十足的肉头随着乳房涌动,在我的背部滑动打
圈,酥酥麻麻的,有些痒,但却让我十分享受。
然后娘亲就整个人挤了过来,光溜溜的地贴住我的背部,可谓严丝合缝。
娘的这个动作从小到大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也许以前我的小鸡鸡还没
有变大也没有长毛,也许那时还没睡觉我就已经很困了,被娘抱在怀里只会更加
快的入睡,靠着那对滑腻似酥的肥乳只会让我感觉更加温暖,更加困倦,哪里会
想其他什么事。
但是今天晚上特别早睡,我现在正精神的时候,哪能睡着,而且我也不知道
怎么搞的,被娘的胸部磨擦时,我居然有一种奇异的感受,心里闷闷的居然像有
蚂蚁在那爬动一样,痒痒的让我难受。
我不知道那是欲火中烧在作怪,只是不自在的扭动了一下屁股,想要离得远
点缓解这种燥闷。
可可能是我扭动带起了风,娘移动了一下身体,居然也挺动屁股,阴阜紧紧
地贴了上来。
我刚开始还没在意,继续扭动了一下,但是我突然感觉到娘的下面好像有一
撮毛,这撮毛在我的扭动下,轻柔的搔弄着我的屁股。
我立刻不动了,我在为自己悲哀,因为我以为女人才长毛,我现在长毛了也
一定是女人。我一直以来都为自己是个男人而骄傲,现在知道自己是女人,那对
我幼小的心灵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呀。
这时靠着我睡的迷迷瞪瞪的大姐说话了:「娘,弟弟老挤我,你让他往后点。」
娘似嗔怪的拍了一下我的屁股,道:「狗儿这孩子不肯好好睡觉,老是乱动
带起风,搞得娘只好越挤越前了。」娘说完,把那只抱着我胸口的手往下一移,
勾住了我的腹部,然后就这样抱拉着往后拖拉了几下。
回到原来的位置后,娘又半压着我,欺身整理我这边的被角,我可以感觉到
那对肥腻绵软的奶子在我身上压扁,以及妈妈突然一条腿跨着我,耻丘毫不设防
的压在我的髋骨处,那撮毛瘙的我好痒,但毛中一团无骨凸出的肥肉滑动拨撩间
却让我好舒服。
这让我心里的蚂蚁越来越多,一种莫名的急躁让我变得很奇怪,我感觉心里
愈发憋气难受,但是却矛盾的想继续接触下去。
娘整理了好一会儿,当我的髋部感受到一阵潮意时,娘却突然叹息一声,再
次抱住我没了动作。
而我回过神来,感觉自己的鸡鸡不知道什么时候肿了起来,而且涨的发疼,
非常难受。我被这种反应吓呆了,我以为我生病了,正准备向娘亲诉说,但是也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一害怕,小鸡鸡就变小了,那涨的感觉也没有了。
我刚舒了口气,娘的手突然再次移到我的腹部,把我整个人用力往她的怀里
挤,接着娘动起来了,她挺着屁股往前拱,紧紧的贴着我的屁股,停顿了几秒,
似乎犹豫什么,最终却下定决心,缓慢的上下磨擦着。
屁股后面那撮毛与其中的烫人绵肉带来了强烈的感觉,搞的我小鸡鸡再次膨
胀,原来还是垂着头的,现在居然笔直的翘起,这是我前所未有的硬度。
娘的喘息明显变得急促,抱住我腹部的那只手轻轻摩挲,摸到我肚脐边不说,
居然还缓缓的往下移动。
能感觉到娘手心汗津津的湿意,她的手越移越低,而我的小鸡鸡居然在这样
的动作下,感觉涨得要爆炸了!
这次我没像以往那样阻拦,不过娘的手在摸到我的那些毛时,我感觉到娘颤
了一下,动作也明显停了一秒,之后她又往下摸,又停下了……
因为她的手掌碰到了我那高高翘起的小鸡鸡,不,倒不如说是大鸡鸡。
娘似乎倒抽了一口凉气,随后猛地缩回手,似乎被蜇到了一样。等了一会儿,
娘虽然呼吸更粗重,但也没什么动作,这让我被窥破秘密的心略微放下。
但是她很快继续抚摸着我那些毛,不过却不再去碰触我那高挺的肉棒。渐渐
地,娘蹭动我的动作有些走样,肥美的娇躯也泌出香汗,量不大,但也有润滑的
效果。
这让娘亲的动作更流畅,她像蛇一样,蹭的我身上也黏糊糊的,让我感觉不
太舒服。但我不敢声张,娘的反常让我害怕。
突然,我能听到耳边一声吞咽香津的靡靡之音,以及之后抿嘴唇的丝粘声。
接着一阵暧昧的暖风吹在我的耳孔里,害我缩了缩脖子,之后我的心里更加感觉
『堵』得慌了。
不过我还是压住内心的忐忑装死,娘亲又试探性的吹了两下,我依旧不理。
娘亲顿了顿,就在我以为她恢复正常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娘那滑嫩的手指在我
的背部写着字,这是很早以前娘为了教我认字,而想出来的一个游戏教学。以我
四年级的程度,立刻就认出娘写的是「长大了」这三个字。
我虽然认出了字,但是非常不解,是说我长出毛长大了呢?还是我鸡鸡翘起
来长大了呢?
我想到这,忍不住好奇转过身来,娘不知道为什么,在发现我想转身的时候
就先一步转过身去了。我那翘起来的大鸡巴立刻顶到了娘鼓胀肥硕的臀瓣上。
一瞬间我下身忍不住抖了抖,这种刺激性的绝妙触感对处男而言杀伤巨大,
我狠狠打了个冷战,一种类似尿意的感觉猛烈袭来,我硬忍着憋住,没敢再动。
但是我发现娘的身子却在颤抖,屁股肉一抖一抖的,我被迫承受着强烈的尿
意。
我赶紧往后缩了缩,夜色下,我看到娘喘息起伏的背向着我,发觉娘不再颤
抖,也没有对刚才的接触表现出不满,我才放下心。
突然,我想,娘突然转身是不是也要我在她背部写字让她辨认呢?
反正我刚好有问题要问,犹豫了下,我就伸过手去,打算在娘光滑的背部写
字。不过接触的一瞬间,娘突然变得很奇怪,身躯又开始微微颤抖,不时痉挛似
得抖一下,似乎在躲闪我的手指。
我老早就知道娘怕痒,看到娘的动作知道她很痒了。我突然有了一丝报复心,
因为娘刚才让我很窘迫。于是我玩心大起,开始轻轻的抚摸着娘的背部、腰肢等
处,上到肩胛骨下到尾椎骨。
娘的身子抖得幅度更大,甚至又像刚才趴在我身上那样扭动起来。但是让我
不解的是:以前我搔娘痒痒的时候,娘早就笑得透不过气来,但是现在她不但不
出声,而且还尽力不让自己大幅度扭动,一会儿躲闪一会儿又迎上我作弄她的手。
我更奇怪,娘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想探个究竟的我开始用双手搔着娘的痒痒,而且我恰巧知道若即若离的轻微
触碰会让人更痒痒,所以我便用上这招。
娘的呼吸变得不均匀了,十分紊乱,她开始往墙边缩去。
玩心大起的我哪能让她跑了,打定主意娘亲不像以前那样求饶就不罢手的我,
紧跟着挪了过去,并且继续作怪,加强攻势。
但是娘却怎么也不肯吭声,而且我摸了一会,娘又撅回屁股来蹭我的大鸡鸡,
我赶紧缩回去。
这让我有些愤懑,突然,我想起刚才娘摸我腹部那些毛的时候,我心头痒得
不得了,看来只有用这招娘才会像以前一样求饶。
于是我的手从母亲臂弯插了过去,开始摸向了娘的腹部。同时我感觉娘的身
上好滑溜啊,暗忖她为什么出这么多汗?炕上虽然暖和,但外面零下几十度的温
度可不是摆设。
就在我摸着娘软乎滑溜的肚皮往下探的时候,一直没有理会我的娘却用手抓
住了我的手。我挣扎了一下,另一只手从母亲身下插过去,这样我就环抱住母亲
了。
而目的,自然还是去摸娘的毛啦。这时娘亲却把我这只手也攥住,我试着挣
扎了下,娘就更用力地抓住我,让我动弹不得。
我急了,想叫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让两个姐姐知道我和娘这么亲
昵。也许以前爹和娘特别溺爱我的时候,我都不会在姐姐面前向爹娘撒娇,可能
是怕姐姐们吃味吧。
于是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解救自己的双手,马上就有主意了。
刚才鸡头捅到娘的时候她可是抖得很厉害,一定很痒。
打定主意的我马上落实到行动上,触碰的瞬间我酸爽的倒抽一口凉气,感觉
鸡鸡马上猛烈的脉动起来,我『自损八百』,相应的『伤敌一千』也作用到娘亲
身上。
娘果然像之前那样颤抖起来。
接着娘触电似地把肥大的屁股缩开了一点,让我的鸡巴不能顶住她的屁股。
我得意了起来,娘果然害怕我的鸡鸡!
嘿嘿……
我知道我找到解救双手的方法了,我的双手环抱着娘的细腰,虽然我没有力
气把她拉过来,但是我却能把自己拉过去啊。我双手屁股一起用力,这个收缩的
动词叫『榨』。
我那猛烈跳动的鸡头终于再次碰到了娘的屁股,这次鸡头擦着汗津津的肥臀
瓣一划,居然滑倒了娘亲的腚沟里,马上我的鸡头就感受到热气、潮湿,以及娘
之后条件反射的肌肉紧绷,被收缩的股沟狠狠夹住。
「啊……嘶……」澎湃的快感让我无法自制的呻吟出声,娘更是如遭雷击,
身躯癫痫似得痉挛了起来,股沟夹得我欲仙欲死,我本能的紧紧抱住母亲,用力
之大仿佛要将她揉进身体里,娘亲则是弓成了虾米状,她嘴里可能咬住了什么,
只是喉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但我却感觉的到她极力压制的艰辛困难。
鸡头触底时,一股滚烫的液体从娘股沟蔓延,不少粘稠的液体浇在我的鸡头
上,然而我可能是涨的太过头,虽然时刻感觉要尿出来了,但堵塞的感觉以及缺
乏尿出来的助力【撸动】,加上我本身感觉尿床丢人极力忍耐,最终母亲打完摆
子我都没有尿出来。
接下来我沉浸在母亲尿床的震惊中,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喘息起伏的背影
缓慢下来,她似乎睡着了,我也不敢说什么,只是鸡鸡依旧梆硬,而且仍深深的
顶在母亲湿热的股沟里。
须臾,母亲突然挪动屁股,似乎要将我的肉棒从腚沟里抽出来,当然,娘的
动作非常缓慢,看来她也不想让两个姐姐知道我们在玩呢,娘还丢人的玩到尿床。
我虽然感觉娘亲的尿脏,但这种时候,特别是我正处在刚才被母亲尿在鸡鸡
上还呻吟出声的尴尬境地,万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于是我也非常配合的往外抽,但是就在我忍着头皮发麻的快感要抽出去的时
候,娘居然……又压低腰肢撅过屁股来,将我的肉棒又套回股沟里!
我感觉到我的鸡巴从离开到被娘的臀瓣吞回去,我心头就涌起一种挺动屁股
的感觉,而且我没忍住,居然配合母亲撅屁股又插了回去。
娘的屁股沟着实够深,我这种尺寸的大鸡鸡居然能顶到底,虽然捅到底的时
候会将屁股肉顶的内陷。
沾着娘的尿,我插进去居然发出了「滋」的水声,即便为不可闻,但在寂静
的夜却也听得到。
我感觉自己有些变态,这么脏……我居然还喜欢这种湿滑顺畅的感觉……
我停不下来了,连续插了几下娘的屁股沟,她却有些吃不住,呼吸带着颤声,
臀部居然又开始退缩,似乎又想吐出我的肉棒来。
玩出味道来的我不管不顾,紧紧贴着娘的屁股前进,终于,娘整个人都贴在
墙角,我被抓住的手都可以感觉到被子那头墙的硬度。我乐了,不拔的是娘,拔
的还是娘,嘿嘿,这次看娘往哪儿跑。
娘终于不能逃了。于是我在胜利在望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把硬如铁的鸡巴朝
娘的屁股挺去。
但是这次我马上发现我顶到娘的屁股沟底部的时候,居然还有陷入的趋势,
而且因为这次我用力大,鸡头感觉挤进了一处火热的肉洞,里面很干涩,摩擦的
生疼。
娘闷哼一声明显僵住了,她的身子猛地一震,紧紧抓住我的双手终于松开了。
而我则感觉到陷在股沟里的肉棒被娘的两块丰满臀部死死咬住了。娘长期劳作,
屁股的肌肉可是很发达的,这种空前绝后的紧绷让我感觉鸡鸡似乎被一张嘴咬住
了。
娘的身子烫人,腚沟里更烫人,热得我只想让鸡巴出来透透气,而鸡头套在
那处肉洞里的感觉火辣辣的很不舒服。
于是我屁股轻轻往后动了一下,把鸡头抽了出来,鸡头和娘紧绷湿滑的腚沟
磨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这让我忍不住想再体会一次。相比快
感,鸡头的疼痛根本不算什么。
想到就做的我立刻挺动鸡巴,这次在我的有意控制下,只顶到了娘的腚沟底
部,没有插入那个干涩的肉洞里。此时我的双手已经解脱了,我立刻把它们抽出
来,来到娘的肥臀上来回抚摸那黏滑带点汗津津的肉感。
大屁股的手感让人着魔,我当然不会摸摸就了事,我找到了娘的屁股缝,用
手把它们往外撑,然后挺动屁股,让我的鸡巴更轻松的挺了进去。
松开手的时候,我又享受到了刚才肉紧的感觉。这次我没有上次那么傻了,
我没有把鸡巴整条抽出来,而是抽出一点,抽出时娘臀瓣紧到居然扯动了我的鸡
皮,似乎不舍得我就这样离去。
我当然也不舍得,马上就猛地挺入,再抽出,如此重复。
而已经完成任务的双手也没有闲着,我一手往上,从娘潮热的腋下穿过,接
触到娘那丰满坚挺的硕乳,用力一抓,五指便陷入肉中,被娘的肥奶『吃了』进
去。另外一只手则从娘的腰部穿过,往下准备去摸娘的毛,完成之前的计划。
接触娘奶子的手,张开的五指一收,指缝马上就夹到娘那特别硬特别大的乳
头,我喘息着大力揉捏了一会儿,就往另外一个奶子摸去,但是却发现,那里早
就被娘的一只手占据了。搞得只好退回原来的阵地防守。
而往下的那只手更加出师不利,还没进攻就发现被娘的另外一只手占领了。
我当然不愿意就这样退兵,试着看对方答不答应组成联合探索队。结果是,我顺
利的摸到了娘肥厚的阴阜,入手一把毛。
那是成竖形排列的毛发,和我成三角形排列的毛不同,到达目的地我便一心
一意的玩起娘亲的毛毛,不过自打感受到阴阜的肥腻厚度,那绵软的手感便让我
爱不释手。之后玩毛倒成了其次,我主攻这团媚肉,并且爱不释手。
这团肥厚的嫩肉,我用小手一抓居然能揪成一团,抓捏的手感一点不比两个
姐姐的奶子差分毫。当然,虽然黏糊糊的毛糜烂的覆盖在上面,但脏兮兮的黏糊
感我却出奇的喜欢。
然而我因为玩娘的奶子跟阴阜,下身忘记挺动,娘却主动筛动屁股,似乎催
促我将注意力放回她的腚沟那边,娘卖力的收缩屁股的肌肉,成功将我的注意力
吸引到鸡巴上面。
于是我再次挺动,抽出插入比之前熟稔很多。就像我性早熟的大鸡鸡,我似
乎对这方面天赋异禀。随着时间,我每抽动一次就带来强烈的快感,这种感觉和
爬杆时所产生的感觉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我的鸡巴很粗,硬起来有15公分,随着抽插,我每次都能探到腚沟底部,甚
至更往前。这时,我发现了底部还有一个微微张开的湿热肉缝,不同于娘的屁眼,
这个缝隙一旦被我的龟头碰触一下后,就如同活物一样收缩。当这个缝隙收紧的
时候,娘的屁股缝就变得很紧密,甚至夹得我的鸡巴有点痛。
而且这个肉缝好湿,肉缝外也非常柔软肥沃,让我很舒服。于是我打算探索
探索。
这样我进攻了那个缝隙几次,就被娘的屁股缝夹了几次,在第四次被夹的时
候,我又感觉到那阵强烈的尿意,好像电击一样的感觉,从脚跟往上涌,先是传
到脑部,然后再传到鸡巴上。
我吓了一跳,娘难道也是因为舒服才尿了吗?但我不能尿啊,娘让我体验到
那么美妙的感觉,我居然想在娘的身上撒尿?就算娘非常的宠我,相信也不会原
谅我在玩着游戏的时候,在娘的屁股缝里小便,再说现在可是在炕上啊,这里是
睡觉的地方,怎么能够拉在这里呢?
我马上吸气,再次咬牙硬忍,同时按住了鸡巴的根部,不让那尿流出来。这
是小时候玩看谁尿得久的游戏时掌握的方法。好一会儿我的尿意终于消失了,我
松了口气,总算尿炕。
几次的尿意让我十分警惕,我想了想,最终害怕尿在娘腚沟里,打算停止这
个游戏。
娘却又撅过屁股来蹭我,这次我却坚定的推了推娘的屁股,娘又试探的顶过
来,我再次拒绝,于是娘不动了。
我原本想转身睡觉,但想了想还是把鸡巴再次插入娘的屁股缝里,娘马上又
扭动起来。我双手抱着娘的细腰不让她动,一手在她背后写『睡觉』二字,娘这
才僵住,叹息一声老实了。
两个姐姐这时睡得很熟,并且还传来她们熟睡的呼吸声。就在我闭眼准备入
睡的时候,娘却突然将屁股抽离,让我的鸡巴退了出来。接着娘回转身来和我面
面相对,虽然在黑暗中,但是我依然能够看到娘那水蒙蒙的妩媚眼神。
娘和我都没有说话,好一会儿,娘伸出手把我推得转过身去,然后在我背上
开始写字了,依照感觉我发现娘写的字有点难理解,第一句是:「小X 生,连你
娘的屁股都干!」那个X 是因为那个字笔画蛮多的,我根本感觉不出来。
我有点呆呆的,因为我不知道「干」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指我那样用鸡巴
抽插娘的屁股缝吗?我似乎明白为什么那些家伙骂人会老是说干你娘了,原来干
娘真的这么好玩的,嗯,不知道干姐会不会也这么好玩呢?
不过,我绝对不会让那帮家伙干我娘和干我姐,要干也只有我能干!我暗暗
的下定决定。娘写的第二句是:「什么时候长毛的?」这话我理解,我转过身来,
这次娘没有转过身去,只是把紧贴我的下体往后移动了一下。我只好在娘的腹部
写了:「一个月前。」
娘又问为什么这么小就会这样,我怎么知道要到哪个年龄才适合这样,所以
我没有回答,只是摸了摸娘汗渍未干的滑溜小腹,接着写「睡觉吧」,我真的很
困。
我迷迷瞪瞪困得不行,娘似乎却精神的很,她的手指又不老实的来到我胸口
摩挲了几下,见我没反应掐了我一下,然后气呼呼的在我的胸口滑动着,飞快的
写出几个字,然后就把我推得转过身去。
我在脑海中仔细思索了一下,才想到这句话是:「没良心。」
没良心?什么意思,怎么就没良心咯?
我刚想转过身去抗议,但是娘已经整好被子,又转身把我牢牢抱住了,一条
腿还搭在我身上,黏糊糊的耻丘压在我身上,报复似得蹭了几下,将我弄得湿湿
的,有些难受。但我很困,也懒得抗议。
过了一会,娘小动作不断的骚扰我,我却稳坐钓鱼台,几乎睡着了。娘突然
一只手穿过我的脖子,箍住我,另外一只手则往下一把抓住我软软的小鸡。
把玩了几秒,我的鸡巴迅速充血,但我却故意装睡,不打算理她。
娘却不打算放过我,撸开我的包皮,摸着大龟头抚摸了一阵,然后松开,好
像试了试自己手中有没有沾到什么东西。我能听到娘吸鼻子的声音,似乎还闻了
闻。接着,那只手再次握住我的鸡巴,轻柔的上下套动着。
虽然被娘用滑嫩的手这样套弄很舒服,但是却比不上娘那紧密地屁股缝。所
以我根本没有一滴尿意,任由娘玩弄的我鸡巴,这方面我的耐力很惊人。
忽然,娘把被子拉起,把我们两人都罩在被子下。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娘的嘴唇又轻轻的贴了上来,她用只有我能够听得到的声音腻呼呼的赞叹:「好
厉害哟……狗儿……居然没有射。」
我不懂什么射不射,我现在只感到很闷,很需要空气,我挣扎着往外钻。娘
看到我的样子,小声哼了下,把被子弄好,松开握着我鸡巴的手,转到我的背后
又写起字来了。
我睡眼朦胧中感觉到那是一句:「刚才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你的
姐姐。」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让姐姐知道,但是内心深处还是认为不让姐姐
知道为好。
于是我点点头,极度困倦的我终于在娘的怀抱中睡着了,在入睡前,我感觉
到娘仍握着我那已经慢慢开始跟着主人休息的鸡巴玩弄着,十分爱不释手。
自从那天的事后,娘与我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之后娘隔三差五便要跟我玩
游戏。我不喜欢那种憋尿的感觉,加上娘的痴缠,让我逐渐变得不喜欢那样腻歪。
几次拒绝,娘终于忍不住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原因说了,娘想了想没说什么,
却答应我,以后不再不经过我的同意『做游戏』了,最后她说,要是我想玩,随
时可以摸她。
娘的身体摸起来还是很让我着迷的,这个提议让我心动,于是我向娘提了个
要求:不许她摸我的时候就不准摸。娘同意了。之后我化被动为主动,开始主导
这个游戏。
就这样,娘的身体变成了我的玩具,让我爱不释手。当然,也有美中不足的
地方,比如每次玩娘的时候她总是尿炕。
娘从第二次起就不对我设防,连下面的肉缝都肯让我扣摸,但有一次我闻了
摸出来的尿,便不喜欢摸了。因为那股腥臊的味道我很不喜欢。
我也问过娘我扣的是什么,娘却只说是尿尿的地方,并且不准我问任何人,
否则她就不让我玩了。不过这样告诉我的结果就是,娘多次让我把鸡鸡插进去我
都不肯,嫌脏。
我奇葩的这么想:娘这么容易漏尿,那么里面还得了?肯定是更加脏的尿包
啊!
可笑我玩了娘那么长时间,却连尿跟淫液都分不清。
随着时间,我开始感觉娘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具体变化我说不上来,只
是知道娘对我比以前更好,更宠了,宠到似乎我要天上的星星,娘都会咬牙答应
并去尝试完成的地步。
我不知道我跟娘是乱伦,而娘知道却隐瞒。于是上天似乎是惩罚娘,违背天
伦的报应很快来了。
过年父亲回来时态度很奇怪,虽然对三个孩子还是很亲,也照常带回很多钱,
但对娘却有些冷淡。对此娘也不在乎,因为重心都在我身上,特别是有一晚爹要
跟娘睡一个被窝,娘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答应,自此爹到走的时候都没跟娘说过几
句话。
而且爹临走前村里就有了流言,并且很快传到娘耳朵里了。说是一个外出务
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主人公就是我爹。说是我爹外面有人了,女方年轻漂亮,
而且是跟他一起做生意的合作伙伴。这时爹已经开始做生意了,那个年代最发财
的买卖之一,诨名叫『倒爷』。
知道消息的当晚,娘就拉着我到没人的地方,抱着我哭诉。
我对男女之情一窍不通,只是傻傻的听着,很小白的说些干巴巴的话安慰娘,
并且心里开始恨爹。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其实爹娘离婚的原因,娘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娘的心已经不在爹身上了,所以虽说是爹出轨在前,但娘
如果在过年时表现的像以前一样贤惠、体贴人,或许……可能爹会回心转意?
当然没有如果,即便有,结果也未曾可知。总之以后爹再也没有回到这个穷
山沟,我再见他的时候是在出事以后,爹从老乡那里得到消息,去城里少管所看
我。这是后话了。
爹走后我跟娘继续保持着『游戏』,有时候我十天半个月不玩,娘看我的眼
神便很奇怪,总觉得灼灼的让人不自在,后来我知道那是饥渴还有幽怨的眼神。
爹的事情也只影响了娘几天,毕竟差不多十年的异地夫妻,谁离了谁都照样
过。
不出半个月娘便恢复如初,而且似乎比以前的笑容还多,往后娘总是洋溢着
幸福。娘往年经常蹙起的眉心我很难再见到,这是好事,但娘的转变让人好奇,
我想又想不通娘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毕竟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对我来说没有半
分变化。
我也问过娘几次,娘就是吃吃娇笑,却也不说为啥。
有一天,我尿憋的很急,就一边脱裤子一边往厕所跑。刚进厕所我已经把硬
邦邦的鸡巴掏出裤子了,我抓着鸡巴刚想尿。天那!娘正在里边尿尿……
我看到娘的裤子卷在大腿上,内裤拉到了圆润的膝盖,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岔
的很开,一股白色的尿液正从黑压压的一片毛中喷射出来。娘的俏脸肉眼可见变
的殷红,剜了我一眼,接着却吃惊的张开嘴呆住,目光显然集中在我的鸡巴上。
娘胯下的尿柱开始不自觉喷的更加激烈,半响,娘才从震惊中回过神。这是
娘第一次在白天看见我勃起的鸡巴,我也是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娘黑毛黝黝的下体,
只是却看不到我经常玩的毛毛里隐藏的肥鲍。
而且娘那么白,毛的颜色就显得格外乌黑,视觉冲击特别强,我一时也愣住
了。
娘咽了咽口水,忽闪着美眸看着我问:「是不是想尿尿。」我不知怎么回答
才好。
娘说:「你要是很急就在这旁边尿吧,我往边挪一点。」说着,娘往旁边挪
了一点,既然娘说了,我就尿吧,我抓着硬邦邦的大鸡巴使劲摁着往下尿,心终
于可以放松了,谁知这一来更难受。
想到每晚,自己用手玩的娘光溜溜、白腻的肥硕大腚,硬邦邦的鸡巴一开始
还摁得住,可我想到刚才看见的娘胯下黑黝黝的屄毛和白色的尿液融合在一起的
情景时,我怎么都摁不住鸡巴了,本就充血的鸡巴变得更大!
最终,一股尿直喷出去,激射到对面的墙上,尿到处飞翔散,溅得娘身上、
屁股上都是,娘被淋得打了个寒颤。是尿太烫了?
但我很忐忑,顾不得想明白烫不烫,我笃定娘这回肯定要生气了。
可娘红着脸咬了咬嘴唇却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情有些懵,软绵绵的扫了我一
眼,便拿了点纸,接着肥硕滚圆的屁股撅向我,使劲擦了两下黑毛中间,就这样
在我身边站了起来,不躲不闪的,扭着屁股提上内裤,穿的时候特别慢,扭动屁
股的骚浪动作让我感觉做作,临走抿着红润润的樱桃小口,紧巴巴的看了我几秒,
这才走了。
不过我还是没看到娘下体的模样,这以后我对那里有了一窥真貌的好奇心,
常常幻想娘的神秘下体,回忆娘两腿间那一片黑茸茸的毛。于是我晚上玩娘的时
候又喜欢摸娘的腚沟,问娘这是什么也更勤了。
娘最终拗不过我,告诉我那是屄,我再问娘屄是干什么用的,娘却羞的难以
启齿,只让我自己把鸡巴插进去体会体会就知道有什么用了。
不过我只是好奇心,对屄内仍感觉恶心,觉得那是尿包,不过这话我没敢跟
娘说,因为之前说她尿炕她就羞恼的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