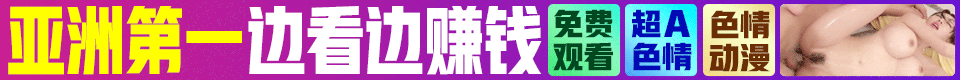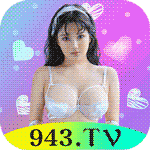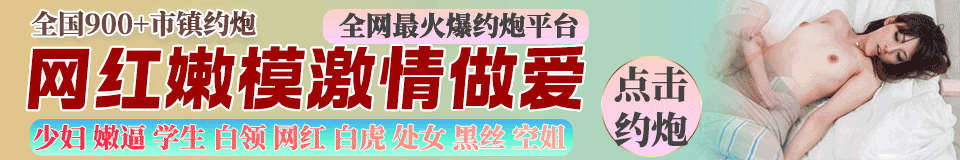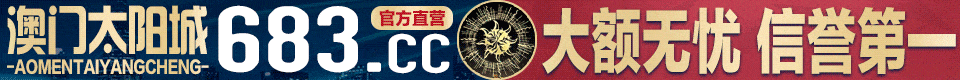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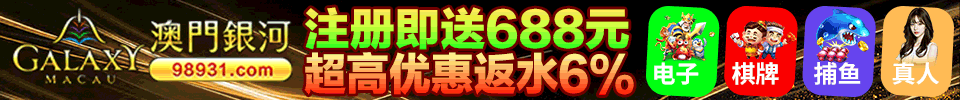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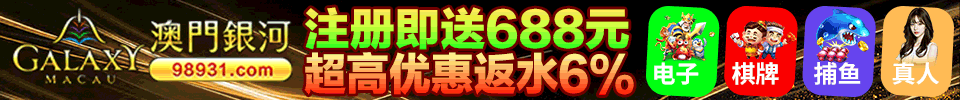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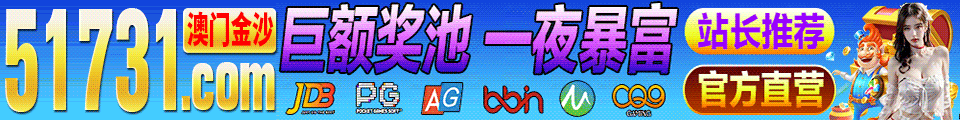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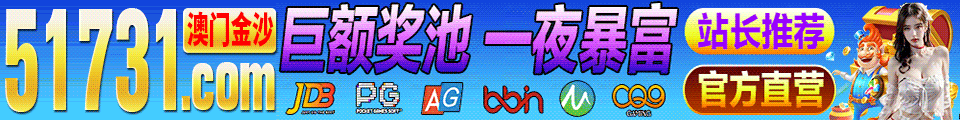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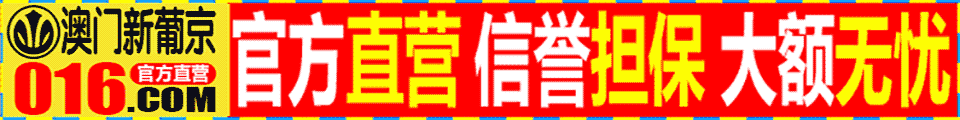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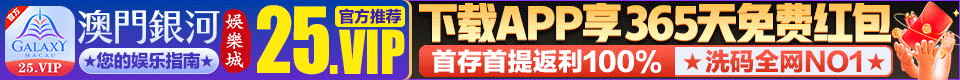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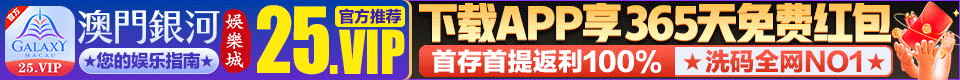











安慰心情不好的女同学
我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大學生,在安徽的某個城市就讀我的大學。
可是,即便是我這樣平凡的人,在當今這個社會中,也同樣擁有過一段不尋常的性經歷。
直到現在,這段經歷作為我生活中唯一的美好回憶,將一直在我心中留存,永遠永遠……那是兩千零二年的冬天,我百無聊賴的在校園安慰心情不好的女同學中延續著我的生活。
我有著很多的好友,他們是我無聊生活中唯一的亮色,有了他們,我才能有些許的快樂。
我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和他們聊天對飲。
(當然,我的這些朋友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不然我的故事就無從發生了)。
有一天,她(暫且以z來代稱吧)知道我又因為學校生活的事情而鬱悶,所以專程來陪伴我聊天解悶。
我們長聊了一個下午,幾乎逛遍了整個校園。
當時正是秋天,有點冷,天也開始昏暗了下來。
看到天色以晚,我們最后決定一起去吃晚飯。
我們一起和兩杯吧,認識這麽長時間,我們還沒有好好的喝過一次,想起來挺遺憾的。
我仔細回想起來,我認識她已經足足有兩年了,我們的交情也確實很不錯,但卻如她所言很需要喝回酒深談一下,畢竟酒是打破人矜持和增進信任的不二法門。
好吧,不過我們今天一定要喝的盡興,喝到醉為止,好嗎?
好的,一言為定!我們學校的旁邊有一家很不錯的燒烤店鋪,是清真的,羊肉串和羊肉湯的味道很是地道,我們最后就選在了那里。
你為什麽總是那麽好,能夠幫我,其實我有時真是覺得自己欠你很多人情。
這大可不必,我一向覺得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才會和你聊天的,你不必覺得欠我什麽,能和你聊天實際上對我也是很有幫助的。
你還是那麽善良,或者說是個性能更貼切些——你的家里最近還好吧?
還能怎樣的,她看起來臉有些紅,不知道是酒的緣故還是她過于激動,我的母親現在仍然被自己的抑鬱症所折磨,也許就我父母本身而言,婚姻就是個錯誤。
不是的,可他們畢竟還是有你的啊!這才是他們更失敗的地方,盡管他們的感情並不牢固,可因為我的存在而不得不維持。
你覺得是不是對他們,甚至對你而言,都是個災難?
而且是無法改變的?
的確,他們這樣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可他們的感情又是破裂的,所以讓我很痛苦。
其實和你相比我的痛苦真的差好多,盡管我的家庭不理解我,可家庭中如果沒有愛,才是真正痛苦的。
她默默的,不再說話,只是慢慢的把杯子里最后的一點酒慢慢的喝了下去。
她的意思我很清楚,她最大的痛苦就是她的家庭,可是即便是人可以改變一切無所不能,卻也沒辦法自己決定自己的父母。
酒是好東西,她好象自言自語,它能讓你麻醉和放縱,忘記很多痛苦。
可是人總是要醒的,改變不了的東西要麽承受,要麽遠離,現在你不是出來了自己工作,自己住了嗎?
是,我就是想遠離家庭,我很羨慕你,而且我想我一定很難結婚,盡管我有###(她男朋友的名字)。
你是因為自己的痛苦,而畏懼婚姻,尤其害怕自己的子女有遭受自己痛苦的危險吧?
恩,她輕輕的說咱們再出去一起轉一轉,好嗎?
很好,我很願意陪你,我最近很有時間。
于是我們離開了飯館,開始在漫步中繼續我們的交談。
其實我的家庭之所以能夠完善和擁有感情大概是因為我的父親,他是我家庭感情的基礎。
我家就是因為我的父親,他……不要說了,我理解你。
我想我以后,一定會做一個我父親一樣的男人,他對感情的忠誠,讓我不得不佩服。
可惜,我卻沒有找到生活中象你父親的人,真是挺遺憾的。
他不行嗎?
說完我就知道自己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她用無言回答了我,答案不說自明,他顯然是不可以的。
過了良久,她說:我可能有點不勝酒力,你能不能扶我一下?
由于我們很長時間來相處的很好,早就將性別拋諸腦后,平時打打鬧鬧的接觸是很多的,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這方面的隔閡。
我于是很平靜的輕輕摟住她的腰,盡管是冬天,我的手依然感覺到她身體那特有的質感,而她身體上那股女性特有的香味也因為近距離的接觸讓我很真切的感受到了。
她不再說話,只是陪我慢慢的走著。
過了一會,我們走到了一座橋上,這座橋上燈很亮,可是路過的車卻因為天晚而很稀少。
我們歇一下好嗎?
她緩緩的說。
恩,不知怎麽,今天我總有種怪怪的感覺,以至于語言變的沒有往常那樣流暢,只要,你,喜歡。
……可是我卻發現,身邊的她眼中不知何時已經含滿了淚,現在這些淚正在滑落,掛滿了她的臉頰。
怎麽了?
我有些慌了手腳,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在哭,在我的記憶里她一向是很堅強的你怎麽了?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把頭伏在我的肩膀上,繼續她的哭泣。
這個時候,也許語言已經沒有了意義,我于是用自己的手絹拭去她臉上的淚,不再說話。
怎麽?
嚇到你了?
當她再次意識到我的存在時,她知道自己哭了很長時間。
沒,看你傷心有沒有辦法開導你,只能由著你,等哭過,可能心里會好受寫。
沒什麽,她一邊說,一邊從我手中拾起了手絹,擦干自己臉上剩下的淚水大概是自己因為對愛情失望吧。
別擔心,不管什麽時候,只要我活著,我都願意為你提供一個肩膀,請不要再哭了,好嗎?
大概是我說錯了話,或者是觸動了她心中敏感的神經,她的眼淚又開始滑落。
可這次她卻沒有伏上我的肩膀,而是默默的注視著我。
我的心里突然不知何故升騰起一個奇怪的念頭:她是個女人,而女人都是脆弱的。
轉念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憐惜,不自主的將她用雙手抱住。
她的頭髮很亂,于是我抽出一只手輕輕的整理起她的頭髮,可是當我的手撫過她的面龐時,卻不受控制的停留在那里,不肯離去。
然后,發生了讓我一生難忘的事情,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竟然輕吻了她的額頭。
我忽然說道:我吻你,好嗎?
她急促的呼吸給了我最好的回答,或者我的意識開始被動蕩的感情所支配。
我和她唇對唇的進行了擁吻!這次是異常激烈的……也許很久之前我就開始喜歡她,只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的左手扶助她的脖子,讓她靠在我的身上,然后輕柔的用這只手在她光滑的脖頸上遊移。
而我的嘴唇和舌頭也在深吻她之后向她的面頰和耳垂繼續著我的愛撫。
我已經不再把她當作單純的朋友,她要成為我的愛人,從今天開始,我要和她作愛。
我的右手則由腰部下移到她豐滿的屁股上,五指張開用力的揉搓。
她的呼吸更加急促了,她的鼻子里開始發出輕輕的恩……恩……恩……哦……的聲音,這更加刺激了我已經高漲的欲望。
我覺得自己的命根子開始挺立。
我開始更加的大膽,我將她抱起放到橋欄邊上,讓她的身體能夠有借力的地方不至于跌倒,而我則能騰出雙手去更靈活的去攻擊她渴望的身體。
我再一次用手將她抱緊,讓她的身體和我的身體面對面毫無距離的緊貼在一起,她的乳房隨著她急促的呼吸在我的胸前上下起伏,讓我的身體受到摩擦。
我從緊抱她的雙手中騰出左手,一個個的解開了她大衣的扣子,然后一下將她的上衣撩起,她那豐滿的乳房盡管還隔著胸罩,可是依然讓我陶醉。
不要……不要……這樣……她產生了本能的害羞和拒絕。
可我知道我們的感情爆發,已不允許終止,而且,她是想要的。
于是我不理會她的反抗,一把拉下她的胸罩,她的乳房馬上在我眼前暴露無余。
可我顧不得欣賞,而是馬上將自己的雙唇貼在她右邊的櫻桃上,左手則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憐愛的撫摩著。
哦……哦……不要……哦……不要……她擡起由于愛撫而變得無力的手,想推開我,可這怎麽可能!我毫不理會,同時加緊了左手和舌頭的攻擊頻率。
哦……啊……啊啊…………不要…………不要…………!她開始陷入快感的包圍中變的開始迷亂和瘋狂,啊………啊…………不…………!不……不要……停!哦……啊…………啊…………好爽…………好…………好…………她不僅神志變的模糊,而且身體也變的主動很多,在不停的用固定的頻率擺動,迎合我的撫慰。
我當然不會辜負她,我一面用右手把她抱得更緊,一面把左手移到她腰間,輕輕的解開她的腰帶。
快…………!我……受……不……了……了……!她 大概是在朦胧之中感覺到了我的這個動作,我……我……要……要…………不能耽擱了!我一把將她的褲子和內衣褪到膝蓋,哇,她的陰戶已經濕潤的不成樣子了,我伸手將中指和食指一下插入她的陰道里,她的陰道真的好緊,而且在感覺到我手指的侵入后猛然收縮,幾乎死死的將我指頭夾住,連做活塞運動都變的很困難。
我高興極了,一會我們一定會很舒服的!哦…………啊…………啊…………啊……………………!!!快…………!我…………我…………要…………要…………要………………!她叫的聲音好大,看來在性事上,她實在很敏感,也很淫蕩。
我忽然有種想惡作劇的沖動,停止對她乳房的親吻,湊在她耳邊問:想要什麽啊?
不說我怎麽給?
操…………操…………我…………快…………快…………!操你哪里啊?
我故意拖延用什麽啊?
我不太會哦!哦…………用你…………的……啊……啊…………雞吧…………操……操…………哦……哦……我的…………小……騷逼……啊……哦…………快來…………我不用再說話了,我現在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開我的褲帶,將自己已經饑渴難耐的小弟弟插入她。
我將自己的龜頭對準她的陰道口,輕輕的摩擦,然后緩緩的插入。
天,一股快感從下體直沖我的大腦…………我開始和她玩命的用力抽插,快感淹沒了我的意識……………………我們終于合而為一,盡管只有一次,可我的心里會永遠記得這一次。
我愛她,但是我們卻沒有緣分,半年后,我們因為她工作的原因而分開,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
我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大學生,在安徽的某個城市就讀我的大學。
可是,即便是我這樣平凡的人,在當今這個社會中,也同樣擁有過一段不尋常的性經歷。
直到現在,這段經歷作為我生活中唯一的美好回憶,將一直在我心中留存,永遠永遠……那是兩千零二年的冬天,我百無聊賴的在校園安慰心情不好的女同學中延續著我的生活。
我有著很多的好友,他們是我無聊生活中唯一的亮色,有了他們,我才能有些許的快樂。
我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和他們聊天對飲。
(當然,我的這些朋友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不然我的故事就無從發生了)。
有一天,她(暫且以z來代稱吧)知道我又因為學校生活的事情而鬱悶,所以專程來陪伴我聊天解悶。
我們長聊了一個下午,幾乎逛遍了整個校園。
當時正是秋天,有點冷,天也開始昏暗了下來。
看到天色以晚,我們最后決定一起去吃晚飯。
我們一起和兩杯吧,認識這麽長時間,我們還沒有好好的喝過一次,想起來挺遺憾的。
我仔細回想起來,我認識她已經足足有兩年了,我們的交情也確實很不錯,但卻如她所言很需要喝回酒深談一下,畢竟酒是打破人矜持和增進信任的不二法門。
好吧,不過我們今天一定要喝的盡興,喝到醉為止,好嗎?
好的,一言為定!我們學校的旁邊有一家很不錯的燒烤店鋪,是清真的,羊肉串和羊肉湯的味道很是地道,我們最后就選在了那里。
你為什麽總是那麽好,能夠幫我,其實我有時真是覺得自己欠你很多人情。
這大可不必,我一向覺得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才會和你聊天的,你不必覺得欠我什麽,能和你聊天實際上對我也是很有幫助的。
你還是那麽善良,或者說是個性能更貼切些——你的家里最近還好吧?
還能怎樣的,她看起來臉有些紅,不知道是酒的緣故還是她過于激動,我的母親現在仍然被自己的抑鬱症所折磨,也許就我父母本身而言,婚姻就是個錯誤。
不是的,可他們畢竟還是有你的啊!這才是他們更失敗的地方,盡管他們的感情並不牢固,可因為我的存在而不得不維持。
你覺得是不是對他們,甚至對你而言,都是個災難?
而且是無法改變的?
的確,他們這樣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可他們的感情又是破裂的,所以讓我很痛苦。
其實和你相比我的痛苦真的差好多,盡管我的家庭不理解我,可家庭中如果沒有愛,才是真正痛苦的。
她默默的,不再說話,只是慢慢的把杯子里最后的一點酒慢慢的喝了下去。
她的意思我很清楚,她最大的痛苦就是她的家庭,可是即便是人可以改變一切無所不能,卻也沒辦法自己決定自己的父母。
酒是好東西,她好象自言自語,它能讓你麻醉和放縱,忘記很多痛苦。
可是人總是要醒的,改變不了的東西要麽承受,要麽遠離,現在你不是出來了自己工作,自己住了嗎?
是,我就是想遠離家庭,我很羨慕你,而且我想我一定很難結婚,盡管我有###(她男朋友的名字)。
你是因為自己的痛苦,而畏懼婚姻,尤其害怕自己的子女有遭受自己痛苦的危險吧?
恩,她輕輕的說咱們再出去一起轉一轉,好嗎?
很好,我很願意陪你,我最近很有時間。
于是我們離開了飯館,開始在漫步中繼續我們的交談。
其實我的家庭之所以能夠完善和擁有感情大概是因為我的父親,他是我家庭感情的基礎。
我家就是因為我的父親,他……不要說了,我理解你。
我想我以后,一定會做一個我父親一樣的男人,他對感情的忠誠,讓我不得不佩服。
可惜,我卻沒有找到生活中象你父親的人,真是挺遺憾的。
他不行嗎?
說完我就知道自己問了一個很愚蠢的問題 她用無言回答了我,答案不說自明,他顯然是不可以的。
過了良久,她說:我可能有點不勝酒力,你能不能扶我一下?
由于我們很長時間來相處的很好,早就將性別拋諸腦后,平時打打鬧鬧的接觸是很多的,所以我們也就沒有這方面的隔閡。
我于是很平靜的輕輕摟住她的腰,盡管是冬天,我的手依然感覺到她身體那特有的質感,而她身體上那股女性特有的香味也因為近距離的接觸讓我很真切的感受到了。
她不再說話,只是陪我慢慢的走著。
過了一會,我們走到了一座橋上,這座橋上燈很亮,可是路過的車卻因為天晚而很稀少。
我們歇一下好嗎?
她緩緩的說。
恩,不知怎麽,今天我總有種怪怪的感覺,以至于語言變的沒有往常那樣流暢,只要,你,喜歡。
……可是我卻發現,身邊的她眼中不知何時已經含滿了淚,現在這些淚正在滑落,掛滿了她的臉頰。
怎麽了?
我有些慌了手腳,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在哭,在我的記憶里她一向是很堅強的你怎麽了?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把頭伏在我的肩膀上,繼續她的哭泣。
這個時候,也許語言已經沒有了意義,我于是用自己的手絹拭去她臉上的淚,不再說話。
怎麽?
嚇到你了?
當她再次意識到我的存在時,她知道自己哭了很長時間。
沒,看你傷心有沒有辦法開導你,只能由著你,等哭過,可能心里會好受寫。
沒什麽,她一邊說,一邊從我手中拾起了手絹,擦干自己臉上剩下的淚水大概是自己因為對愛情失望吧。
別擔心,不管什麽時候,只要我活著,我都願意為你提供一個肩膀,請不要再哭了,好嗎?
大概是我說錯了話,或者是觸動了她心中敏感的神經,她的眼淚又開始滑落。
可這次她卻沒有伏上我的肩膀,而是默默的注視著我。
我的心里突然不知何故升騰起一個奇怪的念頭:她是個女人,而女人都是脆弱的。
轉念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憐惜,不自主的將她用雙手抱住。
她的頭髮很亂,于是我抽出一只手輕輕的整理起她的頭髮,可是當我的手撫過她的面龐時,卻不受控制的停留在那里,不肯離去。
然后,發生了讓我一生難忘的事情,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竟然輕吻了她的額頭。
我忽然說道:我吻你,好嗎?
她急促的呼吸給了我最好的回答,或者我的意識開始被動蕩的感情所支配。
我和她唇對唇的進行了擁吻!這次是異常激烈的……也許很久之前我就開始喜歡她,只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的左手扶助她的脖子,讓她靠在我的身上,然后輕柔的用這只手在她光滑的脖頸上遊移。
而我的嘴唇和舌頭也在深吻她之后向她的面頰和耳垂繼續著我的愛撫。
我已經不再把她當作單純的朋友,她要成為我的愛人,從今天開始,我要和她作愛。
我的右手則由腰部下移到她豐滿的屁股上,五指張開用力的揉搓。
她的呼吸更加急促了,她的鼻子里開始發出輕輕的恩……恩……恩……哦……的聲音,這更加刺激了我已經高漲的欲望。
我覺得自己的命根子開始挺立。
我開始更加的大膽,我將她抱起放到橋欄邊上,讓她的身體能夠有借力的地方不至于跌倒,而我則能騰出雙手去更靈活的去攻擊她渴望的身體。
我再一次用手將她抱緊,讓她的身體和我的身體面對面毫無距離的緊貼在一起,她的乳房隨著她急促的呼吸在我的胸前上下起伏,讓我的身體受到摩擦。
我從緊抱她的雙手中騰出左手,一個個的解開了她大衣的扣子,然后一下將她的上衣撩起,她那豐滿的乳房盡管還隔著胸罩,可是依然讓我陶醉。
不要……不要……這樣……她產生了本能的害羞和拒絕。
可我知道我們的感情爆發,已不允許終止,而且,她是想要的。
于是我不理會她的反抗,一把拉下她的胸罩,她的乳房馬上在我眼前暴露無余。
可我顧不得欣賞,而是馬上將自己的雙唇貼在她右邊的櫻桃上,左手則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憐愛的撫摩著。
哦……哦……不要……哦……不要……她擡起由于愛撫而變得無力的手,想推開我,可這怎麽可能!我毫不理會,同時加緊了左手和舌頭的攻擊頻率。
哦……啊……啊啊…………不要…………不要…………!她開始陷入快感的包圍中變的開始迷亂和瘋狂,啊………啊…………不…………!不……不要……停!哦……啊…………啊…………好爽…………好…………好…………她不僅神志變的模糊,而且身體也變的主動很多,在不停的用固定的頻率擺動,迎合我的撫慰。
我當然不會辜負她,我一面用右手把她抱得更緊,一面把左手移到她腰間,輕輕的解開她的腰帶。
快…………!我……受……不……了……了……!她 大概是在朦胧之中感覺到了我的這個動作,我……我……要……要…………不能耽擱了!我一把將她的褲子和內衣褪到膝蓋,哇,她的陰戶已經濕潤的不成樣子了,我伸手將中指和食指一下插入她的陰道里,她的陰道真的好緊,而且在感覺到我手指的侵入后猛然收縮,幾乎死死的將我指頭夾住,連做活塞運動都變的很困難。
我高興極了,一會我們一定會很舒服的!哦…………啊…………啊…………啊……………………!!!快…………!我…………我…………要…………要…………要………………!她叫的聲音好大,看來在性事上,她實在很敏感,也很淫蕩。
我忽然有種想惡作劇的沖動,停止對她乳房的親吻,湊在她耳邊問:想要什麽啊?
不說我怎麽給?
操…………操…………我…………快…………快…………!操你哪里啊?
我故意拖延用什麽啊?
我不太會哦!哦…………用你…………的……啊……啊…………雞吧…………操……操…………哦……哦……我的…………小……騷逼……啊……哦…………快來…………我不用再說話了,我現在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開我的褲帶,將自己已經饑渴難耐的小弟弟插入她。
我將自己的龜頭對準她的陰道口,輕輕的摩擦,然后緩緩的插入。
天,一股快感從下體直沖我的大腦…………我開始和她玩命的用力抽插,快感淹沒了我的意識……………………我們終于合而為一,盡管只有一次,可我的心里會永遠記得這一次。
我愛她,但是我們卻沒有緣分,半年后,我們因為她工作的原因而分開,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